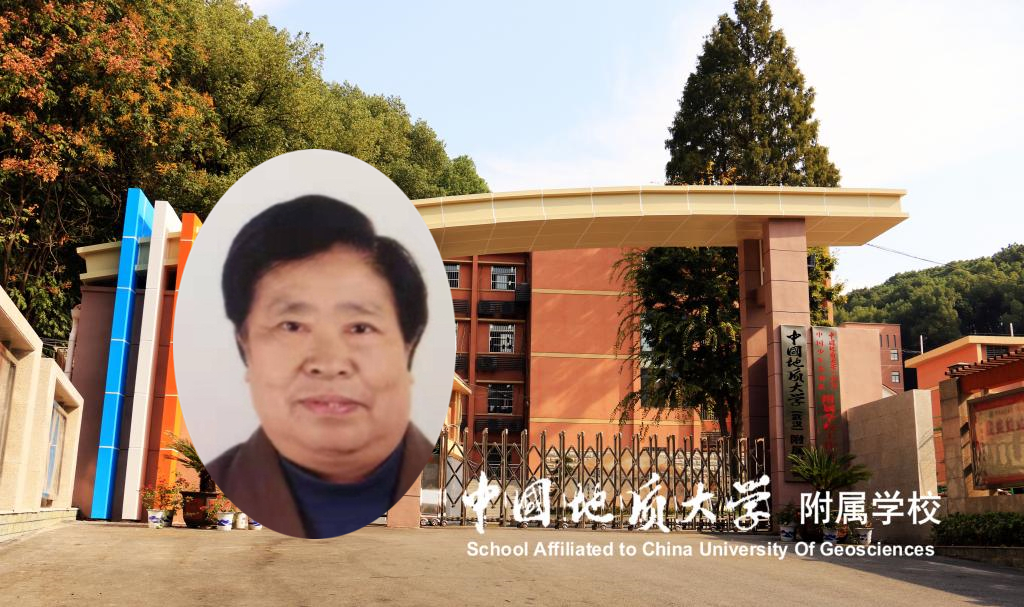
1979年3月,我从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调往武汉地质学院附中。其实,所谓的“武汉地质学院附中”还是虚拟的,连建校地址还未定,我被暂时安排在院办,接着,胡国安、周志华来了,校长邓柴胡来了,教导主任侯超伦也来了,我们就成了“元老”。
武汉地质学院附中说起来也有40年的历史了,我见证了它的成长、壮大。
一所学校,要想提高教学研发成果,使学生掌握该年龄段中应掌握的学习知识与能力,除了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外,勇于钻研、勇于创新的教师队伍也尤为重要。
我在35年的教学生涯中,一刻也没忘记“吃透教材”,从而滋润了自己,提高了自己,也丰富了自己!日积月累,我也慢慢地得到了认可、褒奖、赞许;我渐渐地游刃有余,乃至成为颇受欢迎的老师。
一年,我接受了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任务,我不断地分析研究教材,从而觉得:对于初中来说,学生要掌握好写人、记事、写物的记叙文、说明文,随着年级增长,再加入夹叙夹议,简单的议论文。
学生到了初三,我就从一事一议教学生练习写作。有时,我也教学生夹叙夹议,或者写些简单议论文。
中考前两个月,我集中让学生练习叙议结合的文章,帮助学生审题,比如写《难忘的一件事》中,“难忘”即是题眼,在叙述一件事中,一定要突出这件事为什么“难忘”,就是议论文的成分了。
中考前两周,我们的最后一次作文题目是《生活的启迪》。我让学生写一件生活中的事、人、给自己的启示、教育,我给予了指导并讲评。
中考的脚步近了,我心里反而更加踏实了,因为教材中学生该掌握的,基本上反复练过了。
中考后的一天,家长和学生不时地来看我,原来,中考的作文题是《生活教育了我》。他们抑制不住地说:“杜老师真棒!竟然猜到作文题目了!”
这个好消息不胫而走,家长们的赞许,我听了一点也不意外,什么“神呀!”“棒呀!”只不过是了解教材、吃透教材而已。当然,从中我也得到了欣喜!
另外,我也非常重视教材中文章结构的研究。
比如,初三语文中有一篇课文是“总-分-总”的结构,课后习题还提示学生掌握。我就安排了一次作文课,让学生掌握这种结构特点。我让学生写一篇作文《参观学校的实验楼》。我让学生按下面方法写:①总写: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楼的位置。②分别写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它们为并列关系。③实验楼的功效和自己的心情感想。
我们参观实验楼之后,写了作文,效果不错。后来,我们又写了一篇《我的卧室》,还出了一部《优秀作文选》。
功夫不负有心人!中考送考那天,打铃前5分钟,我聚集了两个班学生,又提醒了一下“总-分-总”结构的那个练习,之后学生踏进了考场。我和家长在考场外慢慢地等待着,煎熬着……
“铃……”语文考试结束了,只见学生吴元元欢蹦乱跳地过来了,她急不可耐地说:“杜老师,你太伟大了!”“那道总-分-总结构的题,考了!”“11分到手!”她继续地说着……“当我看到那道题时,我都要喊‘杜老师万岁啦!’”她按捺不住地说着。家长也群情激奋。我被簇拥着,夸奖着……是啊,这么一场重要的考试,11分该有多重呀!
哪里是什么“伟大”呀,只不过是“教材熟悉”而已。
从此,我更加在研究教材上下功夫,进一步得到学生的认可、夸奖。我也越来越成为他们心中的好老师,从中更加感觉到“吃透教材”的甜头,心中也涌出阵阵欣喜。
岁月在流逝,我已退休二十几年了。我为附中的进步而高兴。后浪推前浪,一辈更比一辈强!
作者简介:杜淑兰,女,汉族,祖籍北京,1940年9月出生,1961年8月参加工作,高级教师。曾获武汉市中学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等荣誉。1995年10月从附中退休。(编辑:刘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