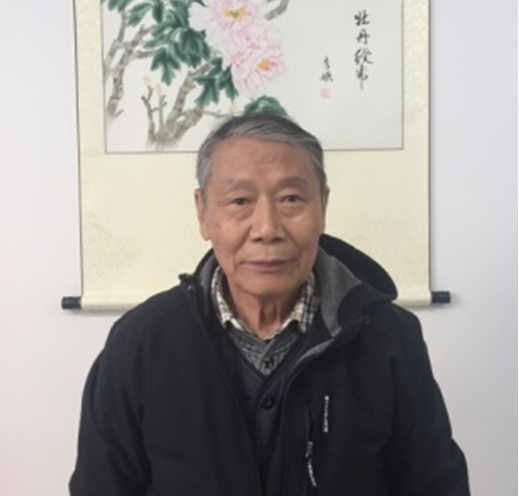
先遣队从江西龙陂出发,辗转三天,风尘仆仆地赶到选在湖北沙洋的新校址。历史上汉江决堤,于河岸向东方向冲刷形成一大片平原,历经长期围垦,该地区成了武汉市农副产品最重要的供应基地,更是闻名全国的七里湖劳改农分场所在地。
我们面对五七干校新校址,目瞪口呆。目力所及,没有柏油路,没有水塔,没有钢筋水泥构筑的房子,有的只是几排东倒西歪的建筑工棚。但见棚顶铺的油毛毡因年久失修风化破碎,棚顶透着亮光。苇子杆两面糊上泥巴做成的围墙,泥巴剥落,四面透风,栓、檀和椽子用粗细不同的楠竹,部分已腐朽,难以支撑重量,摇摇欲坠。这样的棚子类似南方地区饲养鸭子专用的,当时有同志称它为“鸭棚”。这里的一切和征兵队动员搬迁时向大家描述的新址的美景截然不同,但我们既然已经来了,只能尽先遣队职责,抓紧时间,做好接纳后续到来人员的准备工作。
我们先遣队临时借住在路南的新生农场二分场。据二分场同志的介绍,七里湖劳改总场为了安置无法遣返原籍的刑满释放人员,于三年前建成此分场来安置这些人员就业,让他们作农场工人,享受公民待遇,亦能成家结婚生子。据他们介绍,路北的工棚就是当时建分场时用的。我们也向他们请教又快又省的修复办法和所需材抖,最低要求能够住人,还请他们介绍农场周边的地理环境。待到修缮材料陆续到场,我们因陋就简地干起来。最不好解决的是床,从外地购进大量床板是行不通的,我们就想办法把南方建筑工地常用的脚手架拆解,把拆下来的竹片编成床板样子,在泥地打6到8根木桩,然后用铁丝把竹床板固定住,权且当床凑合着用。
我们还在紧张施工的同时,从江西撤出的人员,就按连队编制分成几批陆续进驻了新校址。大家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渐渐地安顿下来,开始了新的五七干校生活。
先遣队从干校范围内3口水井中取水样送检,检验结果显示我们三连水井的水样汞含量超标,不符合饮用水标准。因为人多用水量大,要去路南二分场挑水是不可取的,必须自己解决水源问题,于是连队决定选址打井。此事由我牵头,吴鸿邦设计井图,加上李荫增等共12人组成打井小组。打井作业是2人下井挖掘,2人轮换,8人用滑轮组提升砖瓦沙石和砌井圈。刚开始时,我可以在井下挖掘40分钟,随着井的加深,井下作业20分钟就得上井换人,主要原因是冷,全身起鸡皮疙瘩,肌肉发僵,使不出劲。连指导员买来白酒,下井前先喝一口暖暖身子,但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这样,我们12个人奋战9天,终于挖成一口深15米的水井,并且水质达标。出水量完全能够满足全连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我们便在井台北侧盖了厨房和食堂,东侧是全连的5块菜地,用水十分方便。
经过战士们的共同努力,花了较短时间,五七干校的生活和生产终于走上正轨。大伙回想新校址当初的生活景象,借用一首顺口溜发泄内心的情绪:
说是钢筋水泥砌的墙,
其实是泥巴糊苇杆的墙。
说是柏油路面宽又长,
其实是油毛毡铺在棚顶上。
细雨缠绵下不停,
屋里锅盆接水忙。
床腿长满鲜蘑菇,
鞋子作船漂四方。
干校搬迁过程中,实到湖北的人数比之前大幅减少,只得把原先在江西时的十个连缩编成五个连。我们三连虽然保留了下来,但人员由原先的两百多人减少到不足一百人,并且还有人在陆续离开,如连指导员和副连长等先后走了。其它连队的情况也和我们连差不了多少。
干校的生产活动由校生产组安排实施,日常生活是由各连自己负责解决。干校水田少、旱地多,仅有的八亩水稻田包给了我们三连,一百多亩旱地则由五个连分片包种,种子由生产组负责统一调配,是向湖北省五七干校总校借来的,秋后再还。我们种上了棉花、花生和黄豆。
五七干校1972年的生产任务不算太重,旱地生产活动也比较好进行,所以各连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搞好生活上。今年农作物长势良好,三连种的瓜果蔬菜十分喜人。西瓜、香瓜,既甜脆个儿又大。出工时顺手摘几个,休息时开瓜享受,降温又解渴。自己连消费有余,就送给其他连的同志尝尝鲜。叶子菜更是吃不完,多余的用来喂鸡等。冬瓜结得个个像胖娃娃似的躺在地上,可爱极了,还时不时招来狗和獾捣乱和祸害。经全连决议,我们连先后两次每次一大车菜,支援住在江陵第五石油普查大队队部的校友。
五七干校的第三次秋收季节,三连经过奋战三天,收割完八亩水稻,经过晒干、扬净,共收获三千余斤稻谷,平均亩产400斤,这个产量在当地算是中等水平。
经校生产组协商,请江陵的校友支援秋收,以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大田里种的花生、黄豆收获后,由他们搞小秋收,捡拾落在地里的花生、黄豆。他们返回时,每个人都拎着鼓鼓囊囊的一小包,分享秋收的喜悦。
入秋后,天气很快变凉。武汉夏天是火炉,冬天如冰窖。冬天的冷还不同于北方,人们对于北方冷的感觉犹如刀割皮肤样,而这里的冷是冷到骨头里的痛。去过武汉的同志均有体会,冬天用水时,会冰得让你合着手指蹲下。干校御寒过冬成了大问题。临时解决的办法只能把坚持留在干校的人员相对集中起来,安置到条件稍好的棚子住,并在棚顶加盖一层草帘。这么一改,把鸭棚改称为草棚了。但没有煤炭和取暖设备,已采取的一些防寒措施终究不能解决过冬问题。最终如何解决,还得要找干校领导。哪里去找领导?问唯一留在干校的军宣队员范某某,一问三不知。有同志打听着李指挥长在武汉开会的消息,大伙商量派郭某某、刘某某等5位同志为代表,去面见指挥长。我们留在干校的人员,分在二个草棚,缩着脖子烤火取暖等消息。3天后,他们5人返回,说见不着人,无功而返。这一下更增添了大家的愁绪和怨气,怎么办?只能再派人去试试。推来推去推出有我在内的3个人。干校已处在这种状态了,仍然有人在下面放话,说派代表找领导的性质是请愿,一来运动,就要被清算的等等。我心想,我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找领导反映干校面临的实际困难,要求妥善解决过冬的问题,这会有什么麻烦啊?于是我们3人到武汉先找着给原北京地质学院院长高元贵开车的专职司机陈师傅,向他诉说了干校的现状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陈师傅很乐意伸出援手。他对我们说:“领导在东湖宾馆开会,宾馆门卫认车不认人。”他准备用院长的座驾——黑色别克车送我们进去,他还特别强调要求:“你们的穿着太不符合要求了,一时也无法更换,在车里要尽量趴低一些,不能让门卫发现,否则功亏一篑。”我们一路忐忑,大气也不敢喘,进入宾馆大门,在会议楼前停下,钻出小车方松了一口气。我们把李指挥长请出来,向他禀报情况并转达要求。李指挥长说会议还在进行,不便多说,对我们只说了三点:“①干校人员向湖北丹江、江陵和北京集中,有必要的也可以投亲靠友。②做好干校善后工作。③不能出现人身安全事故。具体如何实施,不久你们也会知道的。”说完他便转身回会议室。我们再三谢过陈师傅,连夜返回,到驻地已是凌晨三点半钟。我们发现草棚里有火星,进去一看,棚里围着火盆坐了一圈人在熬夜等消息。我顿时鼻子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即把李指挥长的指示精神作了传达,大家终于把压在心里的大石头放下了,有的泣不成声。
我们等不及上面派人传达干校收尾的具体安排,用生产组名义开会,介绍武汉之行的情况,要求各连视情况安排人员撤离,做好收尾工作。大家迫不及待地想要早日离开,但是遇到了重重困难。人员三三两两分散走,显不出什么,人数一多且比较集中地撤离,运输就不好解决。干校唯一的一辆汽车早已停摆,司机也回了老家。新生二分场也无力支援。时间紧迫,我跑到4公里外的多堡镇找车行老板谈妥价钱,每天租用5到10辆马拉胶皮轮大车运送行李。人员则去湖北省五七干校总校坐长途公交车到武汉,再转到各人的目的地。大车有专人押送至沙洋码头托运,先运去武汉港,再转运至各户或个人的地址,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特别繁杂,既要把目前在干校的人和行李送走,也要把人早已离开,托付给别人的行李送出去,还要妥善处理没有写明托运地址的行李。这都是我必须做的,是我身为连长的职责所在,更因为我们是走五七道路的战友,是在五七干校共同生活2、3年的同志。
一天,原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王焕,副书记周守成,还有徐新甫(当时不认识)三位到干校。他们代表校领导召集任宝汉、崔武林、朱文华和我等5人开了个会,正式成立以任宝汉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的干校善后工作小组。任务是做完生产的收尾,向新生二分厂办理移交,留守人员三点集中,等待新的任务。会后,三位领导草草看了一眼干校外貌,没有顾及吃饭就坐车走了。
随着人员陆续撤离,开展干校收尾工作时已不到50人。生产任务只剩下一项没有完全做完。要把收获的花生晒干,送还给总干校,抵消春播时借的种子数量,至此,全年的任务才告完成。整理和清点五七干校库存的生产资料和工具、建筑材料、家具和办公用品等。工作量巨大,耗时费力,除了几个大型机械(建校用),所有一切登记造册,一式两份。和新生农场二分厂谈判移交工作过程虽有波折,还算顺利。对方没花一分钱,坐收一笔财富,何乐而不为呢。移交工作进展到最后一段时间,只剩下我们5个人,由二分厂解决住宿和生活。在沙洋度过赴五七道路的第四个春节。大年初一,由二分场场部招待我们吃薄皮大馅猪肉大白菜饺子。
我不知道这一次撤离沙洋,能在什么时间并以什么的方式再回来看看这片土地。卷铺盖走人前该和朋友告别一下。那天我骑一辆什么都响只有铃铛不响的自行车,歪七扭八到酱菜厂找徐干事。我们两个也有二个多月没有看见了,当我告诉他干校已撤了,这次来是向他告别的。相见不易,见着了却要长期分别,彼此唏嘘不已。他强留我吃饭并住下。吃饭时徐干事问我:“来沙洋多长时间了?”我说:“一年加26天。”他接着问:“见过七里湖吗?”我说:“一直没有机会。”他指着饭桌上一盘鱼说:“红烧翘嘴鱼,产自七里湖,七里湖是劳改总场的渔业基地,饭后带你去看看。”我也十分向往。趁天还亮着,我们漫步到湖边,驻足眺望,湖面浩瀚,万顷碧水,微风吹拂,波光粼粼,晚霞投洒湖面,五彩灵动,十分迷人。我们陶醉在七里湖夕阳里。
作者简介:章锦统,男,汉族,浙江人,1937年12月出生。1956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60年8月毕业留校工作,矿床教研室从事矿床学和包裹体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副教授,1996年2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产公司退休。(编辑:张志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