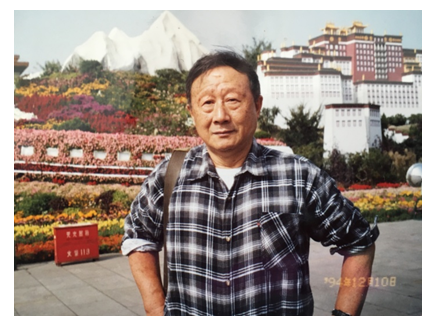
当我和李熙麓同志于1983年4月来到延安市委说明来意时,延安市委宣传部接待我们的同志很感动,说:你们是文革后第一个来延安的高校,有什么要求,我们尽量满足。
有什么要求?!我们是要带学生来受教育的,来吃点苦的!
迁校后,政治师资奇缺,我们就办了一个政治师资班,当时是被逼无奈,现在看来却是一个创举,去延安实习更是一个创举。地质类学生每年暑假要实习,走向大自然,我们的教学计划就是走向社会,拜社会为师。一年级学生暑假我们带去了鄂豫皖老革命根据地红安、麻城,这一程给同学们带来的是震撼,那么多人干革命,前赴后继,牺牲了那么多人,造就了那么多将军。这次时间两周,陈佛香带队。二年级学生暑假我们带去井冈山,这一程给同学们带来的是感动和鼓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次时间三周,曹文满带队。三年级学生,我们要带去的地方就是延安,带队的就是我——凌敬升。预计行程为六周。
我们向延安市委提出:七、八月来,住窑洞,吃派饭,半天劳动,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访谈和革命老人访谈相结合;参观革命圣地还有南泥湾。他们完全同意并决定把我们安排住在枣园村,于是我和李熙麓又去了枣园,见了村支书。村支书很欢迎,表示到时一定安排好。我们向延安市委辞行,市委同志说,在中央关怀下,延安已基本脱贫,解决了温饱问题,枣园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村子,你们的生活没有问题。
1983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19人从武汉向延安进发。带队的是:队长凌敬升,支部书记崔宝成,教师陈玖君、余良耘、李熙麓,还有校宣传部派来的张建忠。学生有13人,北京的张秀荣、王静、李志兵、陈曦凯、宋辉旺,湖北的陈任中、杨尚想、郭清,福建的蔡晓东、林炳政,上海的黄娟,浙江的何显明,还有一位是从武汉市特招的游泳运动员朱维民。
出发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都是乘火车走的。李熙麓先期到达,一切安排妥当,我们向延安市委报到后,就住进了离市区大约十几里地的枣园村。枣园曾是党中央所在地,建在延河的一条支流阶地上,枣园村是由建在山坡上的百十户人家组成。村子有地近千亩,大部分是山坡地,小部分是河滩地,前者耕作粗放亩产不足百斤,后者亩产也只400斤左右。种的都是粮食,只在河滩地种有少量蔬菜。我们劳动都在山坡地上,那里种的是小米,我们的任务是锄草。由于坡度较大,干活时需十分小心,当然坡度很大的地方老乡也没有带我们去。总之我们劳动强度不大,比起在北京拔麦子、锄草、插秧、挑水来说一点也不觉得苦。
苦在吃上,粮食是够吃的,我们也能吃饱。早餐是粥,小米粥或棒子面粥,挺稠的,中午肯定是干的,小米饭或者窝窝头,晚上或干或稀,但都能吃饱。只是基本上没有菜吃,碰巧吃点菜都是煮的,没有油,平常给点咸菜,很咸,一筷子就够了。这就是当时村子里大部分家庭的实际生活状况。我有诸多感慨,同学们也深有感触,深受教育。
住的问题不大,我们19人住了四孔窑洞,窑洞内都有一铺炕,睡上4、5人正好,夏天也不很热,能睡着觉。和我同炕的记得有张建忠、蔡晓东、郭清,还有一位记不清了。我们住的那一孔窑是一排窑洞中最东面的一个,房东住在西面的两孔窑中,只在他们家中吃过一次派饭,串门聊天。再就是挑水,挑了几次不让挑了。挑水,只有我还像点样子,学生们都没干过这活,取水的地方又远,上坡下坡跌跌撞撞,怕出事,就算了。上厕所是个大问题,每天早上我都是跑得远远的,跑到地里,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
在村子里我们组织大家参观枣园党中央旧址。我们住在山坡上,枣园就在山坡下,山坡上没有多少植被,枣园内是绿树成荫,枣树为主。当时枣园是完全开放的,随便进出,有一位老汉看门,还有一位负责打扫。中央首长的窑洞都是一个套间,简简单单干干净净,还有一个小礼堂,据说是周末举行舞会的地方。闲下无事,我们就下山进枣园逛逛,和看门老汉混得很熟。在村里,我们除了分别进行访谈外还和村团支部搞了一次联谊会,座谈、唱歌、照相。
延安市有一条延河,延河在延安市成V字型,转弯处南边有一支流叫南川河,西边有一支流叫西川河,枣园就在西川北岸。离南川大约有15里地。南川和延河的交汇处为市中心,而延安革命旧址多在延河左臂(西)的北岸,从西往东依次为杨家岭、王家坪、纪念馆,还有南边的凤凰山。延安宝塔在南川河东岸。
我们先去了革命纪念馆,了解了延安革命圣地的概况,那是老一辈革命家战斗了13年的地方。引导我们认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支柱。杨家岭主要是去了中央大礼堂,那是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址,我们去时,那里还不是一个旅游景点,去的人很少,所以管理并不严。我们进入礼堂,台上台下可以随意走动,在台上摆个姿势,照个相,留个纪念。随后参观了中央首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旧居。王家坪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所在地,直到1947年3月国民党占领延安,都是人民军队的指挥中心。撤离延安的过程,让人看得惊心动魄,这里中央首长的故居,除毛泽东、朱德的外,还有王稼祥、彭德怀以及叶剑英的故居。在延安,我们还去了清凉山的万佛洞以及延安标志性建筑——延安宝塔。
去南泥湾是我们计划中的一个重点,还是由李熙麓同志打前站,联系好住处和访谈对象。南泥湾在延安东南约50公里,是当年359旅屯垦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展览室,还有一个烈士纪念碑。但是因文革影响,加上年久失修,有所逊色。只是一眼看去全是绿色,山坡上也是郁郁葱葱,保持着当年的景色,告诉人们,这里虽然没有“鲜花开满山”但仍不失“陕北的好江南”的倩影。
纪念碑前留影,山坡上远眺,最难忘的还是拜访了原八路军120师359旅的一位营长——刘宝斋。他曾是南泥湾屯垦的一位战士和指挥官,359旅后来开拔时,他因病未能随队。他给我们讲了当年南泥湾艰苦创业、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故事,讲者生动,听者感动。讲完后我们在他家门前合影留念。
由市委宣传部推荐,我们专访了一位老红军张清义,他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后来转地方工作,我们去时,他已离休。是一位县团级干部。他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讲延安保卫战,十分感人。在他家门前的合影,我至今保留着。枣园村当时(1983年)的村支书叫雷志富,他给我们做报告,主要讲改革开放以来,艰苦奋斗,脱贫解决温饱的过程。
我们离开枣园时说了两句话:第一,认真学习老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第二,希望在坡地上多种果树。
向延安市委辞行后,我们就返程回校了。这一程,历经40天,同学们吃苦受累,深受教育,途经旅游,开阔眼界。
作者简介:凌敬升,男,汉族,江苏人,1935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1951年9月参加工作,1995年8月从文管学院退休,教授。地质系普查专业毕业后留校到地史教研室,三周后转到政治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读研三年,1962年回校任教。曾任哲学教研室主任、政治教研室副主任,社会科学系副主任,校优秀教师。(编辑:张信军)
